綻放在一幅巨大的畫布上,《透明的女性型態》是美國視覺藝術家喬治·康多具有開創性的《素描與繪畫》系列之傑作。作品捕捉了一群華麗的裸體女性好似故障般定格在切換於具象化和碎片化之間的微妙狀態的情景。這幅創作於2009年的精美畫作標誌著畫家開啟其對於《素描與繪畫》系列長達十年之餘的專注,並和諧地融合了傳統上截然不同的繪圖和油畫的創作過程,以此呈現出康多最為代表性的「心理立體主義」和「人工現實主義」。
在《透明的女性型態》中,萬花筒般柔和的霓虹色調灑在大地色的背景上,疊加在麻布上的行動繪畫的即興創作賦予了作品一種節奏感,令人聯想到康多對於在大學時與藝術史同時修讀的音樂的專注。此作中性感的女性形像在畫面中若隱若現:她們的臉頰以雅緻的珍珠為裝飾,豐滿的嘴唇和豐盈的以歎為觀止的流暢性描繪出來。然而,在康多經典的表現方式影響下,帶著奇異的面相、狂野的眼神和破碎的頭像的怪誕角色們,隱約地充斥在背景中。通過這些元素的並置,康多巧妙地將嘈雜的與感性的、可識別的與陌生的聯繫起來,探索慾望、厭惡和好奇等人類最原始的本能。
「『素描與繪畫』是關於線條和顏色中的自由,以及模糊素描與繪畫之間的區別。它們是關於美與恐怖攜手同行的狀態。它們是關於人物型態和其自身意識的即興創作。」
—— 喬治·康多
創作於藝術家作品入選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2010年雙年展的前一年,以及他於新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極具紀念意義的職業中期回顧展的前兩年,《透明的女性型態》標誌著畫家職業生涯和藝術生涯的轉折點。這個時期不單出現了藝術家由個人肖像到眾數角色大畫的轉型,同時也見證了他採用多元化的繪畫技巧以及美學元素。「這些畫布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在於它們將壓克力、木炭和油性粉彩混合在一起到無法區分的程度,還在於它們融合了不同的風格,從而產生了一種表現主義風格的超現實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表現主義風格怪誕的超現實主義。」美國藝術評論家和藝術史學家唐納德·庫斯比特闡述道。「與康多最初成名的個人肖像相比,儘管作品仍然帶著諷刺的意味,現在的康多已經脫離了當時稚氣的漫畫式風格。」i
「我試圖同時描繪刻畫出一個角色的各種思路 —— 歇斯底里、喜悅、悲傷、絕望。你若能夠一眼看到當中的所有內容,我的藝術便達到了我試圖以之達到的目的。」
—— 喬治·康多
康多的畫作並非用來刻畫特定的人物,而是使他的研創可視化的平面。他淺談道:「它們不太是獨特的人物,而是從人性當中所觀察到的情感,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它們是變量,可以隨時互換。」ii 康多通過他獨特的素描與繪畫的創作方式,保留了他的標誌性風格。他聲稱,「能夠同時看到人類性格的多面性就是繪畫所提供的、在真實世界中無法探索的可能性,而你可以以此捕捉到我所說的心理立體主義。」iii
據藝術家所言,「素描與繪畫系列 … 是對於素描和繪畫兩者之間存在的持續的等級制度的反應。我想做的是把兩者結合起來,把素描和繪畫放在一個水平上,讓兩者之間沒有真正的區別。通過將粉彩、炭筆、鉛筆和所有這些不同的繪畫媒介結合在畫布上,對於觀眾而言,能夠看到素描和繪畫可以共同存在於一個——我會稱之為——快樂的連續體中,這將是一種體驗。」iv
作為一名年輕的畫家,康多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居住在巴黎時,研究了他的偶像巴勃羅·畢加索的作品,吸收了這位立體主義大師無論是在技法上還是在構圖上的大部分表現手法。像畢加索一樣,康多帶著有點違反直覺的目標,試圖通過拆解和重新組合的創作過程來更準確或全然地表現他的主題,以此重振肖像畫。在《透明的女性型態》中,康多通過使用讓人聯想起他的前輩畢加索的分析型立體主義畫作之柔和中性色調,向這位現代主義大師致敬。然而,這片單色調的廣闊畫面被似乎撕裂畫布的如棱鏡般七彩的色調所打破, 體現了康多標誌性的「心理立體主義」的「心理」方面。「我不想簡單地看著牆上的畢加索或閱讀有關畢加索的書,」康多沉思道,「我想真正地通過他來作畫,我想畫入畢加索。」v
該作的構圖、女性裸體挑的姿態,以及屬於立體主義派對於背景碎片化的處理方式,都不禁令人聯想畢加索極具標誌性的《亞維農的少女》。其中亞麻布的色調質感讓人想起畢加索常用的大地色和肉色之色調。然而,圓潤的、理想化處理的裸體則暗示了古典寓言繪畫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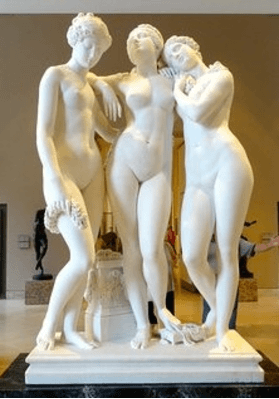
欣賞《透明的女性型態》時,多種藝術時期的元素浮現在腦海中,當中包括古典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其中一個明顯的借鑒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中最典型的構圖元素,例如桑德羅·波提切利著名的《春》當中三位仙女聚在一起,成為大畫面中可以單獨劃分出來的小構圖。康多也如《春》中一般將自己的三位裸女 —— 也許是在西洋畫史最具代表性的象徵 —— 放在畫面的左側,隱喻古典大師畫作中的這個構圖比喻。
「音樂佔據我生命的一大部分,如果是沒了它我都不知道我會不會執筆畫畫。」
—— 喬治·康多
康多就像一位偉大的爵士音樂家重新詮釋流行旋律以表達自己獨特的情感一樣,來進行他的創作。音樂,尤其是爵士樂和古典樂一直都是藝術家重要的靈感源泉之一。就如他自己所言:「音樂佔據我生命的一大部分,如果是沒了它我都不知道我會不會執筆畫畫 … 我最喜歡的事情是在工作室裡放一張唱片,然後在沒有註意到音樂已經停止播放了幾個小時的情況下仍然在畫畫,這期間,音樂只是在我的腦海中流淌。」vi
畫面中捕捉到的無定形的過渡狀態讓人想起與爵士即興創作的那種活力、轉瞬即逝以及流動性。 康多流暢、自由渲染的線條,輔以看似偶然的顏料塗抹與疊加,在視覺上生動地捕捉到了爵士音樂所傳遞的生機勃勃的能量。同樣將這種能量變得顯而易見的是美國視覺藝術家小阿奇博爾德·約翰·莫特利在其標誌性作品《夜生活》中,對芝加哥南區一家爵士夜總會充滿活力的場景的描繪。帶著對其各自生活時期的獨特風格的參考,兩位藝術家充滿激情的創作都是通過形態與色彩複雜的重疊,以及明暗對比來傳遞的。受到美國寫實主義畫家愛德華·霍普的《夜遊者》的啟發,莫特利選擇以深色調作為基調,喚起夜晚親密的氛圍,而康多極具當代特色的柔和的霓虹色調則將他的創作定格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